采写︱张弘
中国很早就形成一个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既重叠又互相支持的完整系统,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颠覆性的冲击,它总是能自己调整,也就是始终"在传统之内变"。所以,外面的知识也好,宗教也好,思想和文化也好,很难零敲碎打地改变中国,而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也很不愿意简单实用的"拿来主义"。……外来文明冲击,必须是整体的、强力的、让中国人觉得是真正比自己高级的,甚至还得有"坚船利炮"加持,才能让中国"在传统之外变",否则传统不太容易被改变。
菩提达摩被称为中国禅宗始祖,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显示,禅学传入中国不始于达摩。
近日,著名学者葛兆光教授的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初版1995年面世之后,即引发了学界广泛关注,2008年出版了修订版,而今年的再增订版除了增加一篇长序之外,还替换了一篇附录,对原来的注释和史料征引做了较大的核对和修订,并且对文字再次润色和删改。一部著作二十多年之后仍然魅力不减,这是对其学术价值最好的证明;每次再版都认真修订,由此可见葛兆光教授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信仰者所述的佛教史,往往因为过多的温情和敬意而不够客观,层层积累而缺乏怀疑的眼光;其次,史家对佛学的研究,更注重的是历史学的方法,努力还原佛学在历史现场的实际情形;再次, 本书对这一时间段禅思想史变迁做细致分析的同时,也涉及了禅宗各派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见到400年间禅宗兴衰及其思想的发展过程。 采访葛兆光教授是我很久的心愿。大约20年前,我曾经编辑过两册和佛教有关的图书,其后也读过一些相关著作。阅读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之前,刚好读完了学者马勇的《中国儒教三千年》,其中部分内容和佛教相关。尽管如此,阅读40多万字的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仍然让人受益匪浅——尽管它只是二十几年前的著作再版。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当下,准确理解和认识传统的中国思想是必不可少的功课,而葛兆光教授的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两卷本《中国思想史》,以及《宅兹中国》等等著作,都不失为重要的参照。 采访葛兆光教授之时,他在封控的上海家中足不出户,恰好修订《中国思想史》的中古佛教部分。就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一书,以及《中国思想史》相关部分涉及的问题,葛兆光教授对燕京书评的采访一一作答。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1950年生于上海,1984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何为中国:疆域、族群、文化与历史》等。
燕京书评:作为思想史学者,你的研究方法与佛教人士的"内部"研究有何异同?
葛兆光:坦率说,我并不是佛教专家。记得1980年前后,我还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就跟我说,两门学问不能碰,一是"红学",二是"佛学",都是无底洞,深不可测。他虽然有点儿开玩笑,但是说得也有道理。我对这一点很有自觉,所以,我要一再声明三点: 首先,我不是研究佛教或佛学,而是研究和佛教相关的历史,这一点你在《中国禅思想史》里也能看得出来,重点是在历史。以前,胡适、陈寅恪、汤用彤他们,其实都是这样的,他们和杨文会、太虚这些人不一样,研究佛教不是因为信仰,和欧阳竟无、吕澂也不一样,也不主要是讨论佛教哲理,研究的重心是历史,所以,我在《(再修订本)中国禅思想史》的代序中,用的就是"在胡适的延长线上"这个标题。 其次,仅仅是佛教历史,也很长很复杂,我掐头去尾,因为没有受过那种特别的语言训练,所以我基本不敢碰印度佛教,即使是汉文佛典和中国佛教,其实,也只对三个时段的历史和文献有兴趣:一是中古佛教,因为它是佛教进入中国,与儒家、道教互相冲突融合,并在中国生根的时期;二是宋代以前的禅宗,从1980年代我写《禅宗与中国文化》以来,我就始终对这个被称为佛教中国化的关键时代有兴趣,而且禅宗史可以作为重新改写被攀龙附凤的历史,综合传世文献、石刻资料、敦煌文书进行史料批判的绝佳领域。当然,现在禅宗史研究的热点逐渐转移到宋代,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黄金时代的唐代禅宗,基本上是宋代建构起来的,像Morten Schlutter的How Zen Become Zen,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不过也多少有点儿太后现代,我还是觉得,通过历史和文献,可以摸清唐代禅宗历史;三是晚清中国佛教的复兴,以及它与日本佛教的关系,因为我1990年代几次去日本,刚好看了很多日本这方面的文献和论著,觉得这是一个过去关注不够,但是,对现代中国思想很有影响的事,可以拿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宗教转型来做比较。
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
作者: 葛兆光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2年1月
内容简介:本书以历史学与文献学的方法,叙述6—10世纪中国禅思想史的脉络与演变。作者综合禅门史料、石刻文献、传世文集和敦煌文书,从历史、思想、文化意义及影响三个维度,考证、叙述禅史关键的四个世纪中,禅宗及其思想的历史变化过程。在20世纪以来禅宗史研究的基础上,不仅修正了此前禅史研究的若干结论,而且对禅思想的内涵及其意义,提出若干与前人不同的新看法。
燕京书评:用许理和的话说,佛教征服了中国,《中国思想史》在承认这一面的同时,也谈及了中国融化佛教的一面。有学者认为,佛教从公元1世纪传入中国,到宋代真正融入中国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如果此说不差,那么它似乎显示,文明的融合、观念的碰撞和普及需要足够的时间和其他条件,其间可能会一波三折——例如《中国禅思想史》再增订本中提及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周世宗灭佛(三武一宗灭佛)。除了道教和佛教的宗教竞争之外,统治者为什么要灭佛?佛教融入中国的成功案例,对于外来知识、思想和信仰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葛兆光:关于这个话题,请允许我扯远一点儿。 你知道,古代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相对完整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你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就可以了解,殷周之际历史方向的大变动,让古代中国很早就形成一个特别的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系统,就是所谓"礼乐文明"。到了秦汉建立大一统帝国、实行郡县制、强力推行"行同伦、书同文、车同轨",逐渐把这个儒法合一的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系统从上到下,加以制度化、意识形态化和世俗生活化,这就是我常说的,思想史应当注意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有人说是这是"早熟",好像马克思也那么说过,不过这个词儿不太好,因为"早熟"就好像另有一个"正常"的,而中国好像不那么"正常",像个早产儿似的,所以我只能说,它确实很早就形成一个政治、思想、社会和文化既重叠又互相支持的完整系统,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颠覆性的冲击,它总是能自己调整,也就是始终"在传统之内变"。所以,外面的知识也好,宗教也好,思想和文化也好,很难零敲碎打地改变中国,而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也很不愿意简单实用的"拿来主义"。尽管鲁迅早就说过这种"拿来主义"有好处,但传统中国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总是要有体有用,有道有器,有本有末,用我的话说就是有一种"整体主义"的倾向。你看,晚清民初一直到当代的李泽厚先生,为什么老是要讨论"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其实就是因为中国知识人习惯于,要整体理解和接受另一种知识、思想或信仰,不能简单拿来就算,这就导致了所谓 "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有人说,传统中国文明就像一个一字长蛇阵,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外来文明冲击,必须是整体的、强力的、让中国人觉得是真正比自己高级的,甚至还得有"坚船利炮"加持,才能让中国"在传统之外变",否则传统不太容易被改变。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很不一样,大概比较早就形成系统的文明,要改变都不那么容易。 所以,中古时期佛教进入中国,也应该这么看。严格意义上说,对传统中国产生整体冲击,大概历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中古的佛教传来,一次是晚清的西潮冲击。中古佛教传来,就是外来的另一个文明对本土文明体系的整体冲击。但中古时期的佛教传来,不像后来晚清时代,一方面清廷自己已经衰落得不行,另一方面那时的外来文化,除了先进制度还有"坚船利炮"。所以,中古佛教进来,冲击是冲击了,但这只是"软冲击",中古中国的反应就和晚清中国的反应不同,晚清是没办法,不变就亡国亡种了,不得不两只脚都走出去,这就是"在传统之外变"了。而中古时期对佛教回应的时候,则还是我强你弱,仍然可以"在传统之内变",也就是可以自我调整,渐渐适应,然后改造你外来的东西。所以,我并不完全赞成"佛教征服中国"的这个"征服"说法,我在《中国思想史》中就说,佛教进入中国,与其说是许里和说的"征服(Conquest)",不如是陈观胜说的(被)"转化(Transform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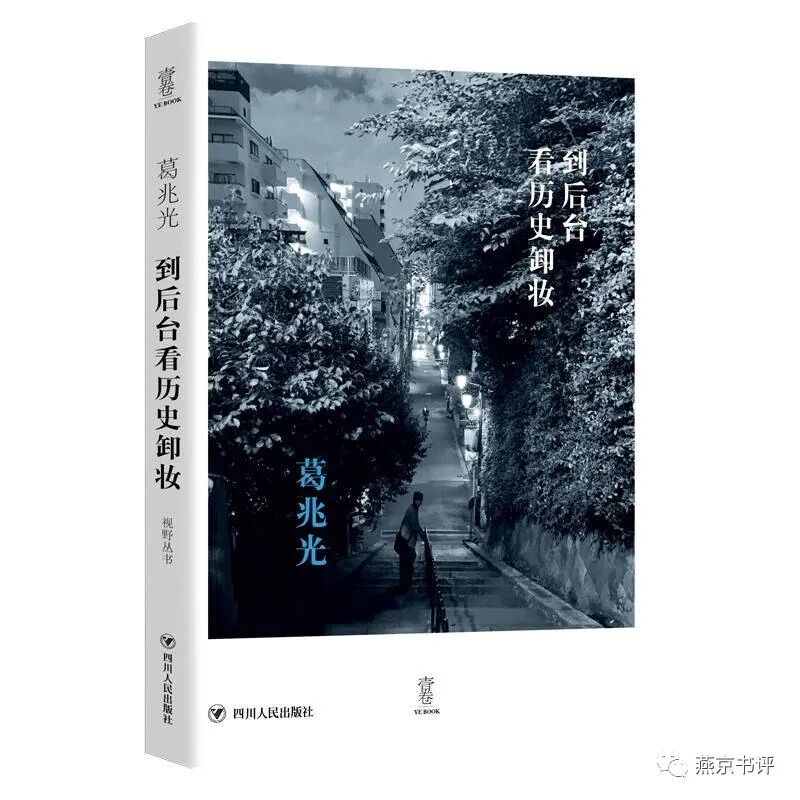
《到后台看历史卸妆》
作者:葛兆光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11-01
扫码下单
燕京书评:在西方国家,基督教相当长的时间凌驾于世俗国家之上。即便在政教分离之后,也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而不是王权的附庸。但是,《中国思想史》《中国禅思想史》显示,无论是汉代形成的道教,还是传入中国的佛教,一直受到皇权的管控和钳制。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包括禅宗,也包括儒家),皇帝喜好或推崇即兴,皇帝厌恶则处于边缘。为什么?
葛兆光:这就是中国和欧洲在宗教、政治与文化上结构性差异之一。在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很悠久的政治传统,所以,我把东晋末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引起的讨论,看成是中国思想史上一等一的大事因缘。经过几百年反复争论,最终还是传统的政治伦理压倒外来的宗教信仰。按照唐代初期士大夫的说法,佛教在古代中国传统中,一方面对父母是不孝,一方面对君主是不忠,而"人伦大者,莫如君父",如果这样,它很难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立足。所以,有关"沙门不敬王者"也就是宗教与皇权的争论,最终在唐代见了分晓。唐高宗显庆二年(657)朝廷规定,宗教徒必须礼拜王者,而父母与君主不用礼拜僧尼,也就是说宗教必须服从政治。到了唐玄宗天宝五载(746),更宣布"以官辖寺,以寺辖僧",用官方掌握的度牒,注明僧人名号及所属寺院,以证明身份,等于让僧尼道士也如同编户齐民,这更限制了宗教徒的组织与行动自由。这说明什么?说明政治还是在宗教之上。就连管和尚道士的和尚道士,也仍然要由朝廷任命,说你是几级几品,就几级几品,让我不高兴,我就灭了你。你别看中古石雕有《礼佛图》,好像君王都朝拜佛陀。你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在大厅一眼就能看到的,一面是山西佛寺的巨大壁画,一面就是中古的《礼佛图》石雕。可是实际上,政治还是裁判一切的,你看雍正皇帝,他对佛教道教的评判,可不都是居高临下的? 有学者说过,这一点影响特别大。因为在政治上,中国的皇权三合一,也就是史华兹和林毓生讲的,是Universal Kingship, 他既是政治最高权力,也是宗教神圣领袖,还是知识的垄断和裁判者,所以有人形容,他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如果是在欧洲,宗教和王权彼此对立,形成互相制衡的两极,就像围棋有两只眼是活的。你一旦在宗教上受到压抑,你可能在王权下逃遁,你一旦政治上受到压抑,你也可以在宗教中得到精神庇护。可是在古代中国,宗教没有什么力量,它匍匐在皇权之下,你看佛教寺庙门外大墙上,都要一面写"法轮常转",一面还要写"皇图永固"嘛,所以你无所遁逃。 其实,中国不光和欧洲不一样,和日本也不一样。你别看日本文化受中国影响,其实,就像丸山真男说的,有"深厚的古层"和"执拗的低音"始终在修正、在改造外来的文化。日本的宗教不光有"神佛习合"这样很日本风的特色,而且他们进入政治很深,宗教领袖的地位很高,宗教的独立性很强,甚至宗教还有自己的武装,禅宗和尚还总是担任国家的外交官员和外交使节。有一个故事很有代表性,就是日本的白河法皇(1053-1129)就曾说过,当天皇虽然神圣,但也有"三不如意",就是再神圣也管不了贺茂川(鸭川)的水、双六(陆)的赛(目)和山法师,其中"山法师"指的就是延历寺的僧兵。所谓京都的延历寺和奈良的兴福寺,叫作"南都北岭",非常强横,和诸侯没有两样,所以,1571年统一了日本南北的织田信长(1534-1582),要火烧延历寺,攻打大阪的石山本愿寺(在今大阪)织田信长要强化将军的权力,统一全日本,就不得不向日本的佛教宣战,这是因为当时佛教寺院势力太大。有人可能了解,日本史上有所谓"显密体制",1970年代日本学者黑田俊雄就提出过日本史上这种特别的现象,这个概念在理解中古日本史,甚至近世日本的时候,都很有用。日本的王权与神佛,虽然不像欧洲教廷和国王那么明显二元,但是一显一密,也和中国不一样。因此,宗教对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还是很重要的,在明治维新的时候,要支撑天皇和国体的神圣性,是靠外来宗教还是靠本土宗教,才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才有了"神佛判然令"这样影响政治局势走向的,关于宗教问题的制度,才会有把神道教当作国教这种强化天皇和国家神圣性的举措。

禅宗六祖慧能像。
燕京书评: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曾经以其深邃的义理,完整的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性吸引了一部分人。这既有宗教信仰的原因,也有知识和思想上的吸引力(《中国思想史》、第一卷564页)。但是,8世纪以后,中国佛教的理论兴趣衰退,禅宗瓦解了宗教的严肃性和深刻性(《中国禅思想史》460-461页)。最深奥最深刻的唯识宗寿命最短,以义理分析见长的三论宗、华严宗信众不多,而方法直接、义理简明的天台宗、禅宗、净土宗信众较多。除了人性天然的趋易畏难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葛兆光:历史学者很怕从人性、性情、感情这些不太能确定的因素上分析问题,因为那些因素一般无法实证,而历史是讲证据的。你说,人们"趋易畏难"的天性,造成某些宗派兴盛,某些宗派衰落,我也相信,从感觉上来看可能是真的。但是,作为严肃的学院的历史分析,不好这么说。我们还是需要从理解和接受佛教的中国思想土壤,上层文化人与普通民众的兴趣差异,以及皇权的支持与否,佛教某个宗派有没有出现过杰出领袖和思想天才这几方面讨论,特别是,要从那个时代的知识风气和文化背景去分析。
我举两个例子。比如,你说唯识宗寿命短,因为它太深奥最深刻,学起来很难,但晚清民初为什么唯识学却突然非常兴盛了呢?如果你从当时面对西学,唯识学的细密分析可以回应西学,可以鼓舞东方信心等方面去分析,你就知道,为什么杨文会他们为什么要急着从日本收集中土长久遗失的唯识文献,章太炎这些人为什么要吭哧吭哧地去啃艰难的唯识著作;又比如,你没有提及的密宗,在唐代据说是"三传而绝"。也许,三密相应、阿字观、月轮观这类神秘主义宗教风格,有点儿不适合中国文化人很早就有的"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传统,可是,为什么在日本真言宗却始终长盛不衰?到了民国时期,中国还得派出僧人去日本高野山学习。这恐怕也有时代背景和文化土壤的问题。
前面我说过,对于佛教研究来说,我太偏重历史。我不能说其他方法和途径不好,不过我说过,我还是在胡适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延长线上。其实,这也是思想史的路数,分析思想的"语境",就是剑桥斯金纳提倡的思想史方法,它把"史"这一面给突出了。 
《古代中国文化讲义》
作者:葛兆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1-01
扫码下单
燕京书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512-526页)分析了佛教传入中国后吸引很多信众的原因,但我想到这是否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社会地位低下的下下人)生存压力巨大,生活贫困,而专制统治和等级秩序,以及宗法制对民众形成了种种的人身控制,入汉以后的儒法合流又使得官方意识形态对民众实施了精神上的操纵。在无可逃遁的君主制下,绝大多数底层民众既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希望,现实中的生存乐趣也极少。在此情况下,佛教向民众许诺了一个美好的死后世界以及积德行善换取更好的来生,一方面使人淡化了生存的痛苦,接受悲惨的命运;另一方面又使之接受现实世界中的种种控制和规训,用善恶报应等等自我安慰。你怎么看?
葛兆光:佛教在最初是怎么吸引信众的?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梁启超先指出,佛教能兴盛,能吸引人,一方面和它借助巫术就是所谓"咒法神通"之力有关,所以"只有宗教的意味,绝无学术的意味",一方面和战乱有关,就是你说的那些"看不到希望"之类的社会原因。稍后,汤用彤也指出,佛教之所以在中古时期大盛,一是方术的力量,二是胡人政治泯灭华夷界限,三是祸福报应深入人心。这些都很对。所以,我前些年给研究生讲课,曾经专门讲《魏书释老志》,讲义后来在刊物上发表了,我觉得,中古佛教之所以能够吸引信众,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佛教最初进入中国,确实是依傍了传统方技数术,也就是民间巫术的力量,靠神奇吸引信仰者;二是这个外来宗教能传播开来,确实和当时异族入主中原有关,汤用彤说的没错;三是佛教传播迅速,也因为那些祸福报应之说,既有切身的浅显道理,他们也有高明的宣传手段。这三点都和前人说的没有差异,不过,我还说了第四点,就是佛教信仰从星散的到系统的传播,以及佛教纪律的成熟和它教团的组织化。像道安定《僧尼轨范》,让信众有了组织、制度和规矩,就不是打游击的野和尚了,这样,佛教就站住了,既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也受到了民众的敬仰。 其实这些个说法,就是过去说的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分析方法。至今我觉得大体上没有错。当然,是不是可以再深入一些?你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古的佛教之所以能吸引很多信众,除了"许诺一个美好的死后世界"和"积德行善换取更好的来生"之外,还有实际的措施,比如出家之后,寺院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自给自足,成了僧祇户,不在朝廷版籍之中,可以免除赋税,寺院又有长生库,荒年可以安度。后来,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是不是和这个有关?而朝廷不时要打击佛教,包括一些官僚要限制佛教,也大概和这个原因有关?我记得,以前何兹全、谢和耐他们,都研究过这个方面。
禅宗七祖神会。
燕京书评:庄子思想、魏晋玄学和禅学之间,在观念上存在着很多类似或相似的地方,知识精英(上上人)追求自然适意的心灵,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中国禅的产生和兴盛。是否可以说,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通过统治者和精英阶层认可和传播,有意开设方便法门以实现这种交易?
葛兆光: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多说几句。佛教尤其是禅宗,他们开设方便法门,是不是"为了通过统治者和精英阶层的认可"?我们分两方面说。 一方面,通过统治者认可,这并不一定非得要方便法门不可。我们看历史上佛教得到皇权认可和支持的例子,像南方讲义理的佛教得到梁武帝支持,靠的恐怕不是方便法门,而是深刻的道理、玄妙的解说和标高的理想;又比如禅宗,神秀和神会,北宗和南宗,一个是渐修一个是顿悟,并不一样,也都得到过皇帝的支持;我在《中国禅思想史》里讲到南宗禅最终胜利是在九世纪初,但是不是南宗禅的道理说服了皇帝呢?未必。皇帝考量接受哪个宗教,怎样安顿各个宗教,我想还是政治考虑比较多。包括是不是有利于稳定统治,是不是可以增加皇权的神圣性,是不是对国家经济税收有影响,是不是有利于地方社会的秩序稳定?你看宋孝宗说的,以儒家治世,以佛教治心,以道教治身,大体上是从实用考虑的。以前我读季羡林先生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的序,他分析唐高宗、武则天时代,佛教为什么得到王权的支持,我觉得他主要是从社会史、政治史的角度说的,但说得大体不错。他说,宗教对于王权的作用,才决定宗教在中国的荣辱盛衰。宗教对于王权的用途,包括六方面:第一,哪个宗教拥立了自己?第二,哪一个宗教对眼前或将来的统治有用?第三,哪一个宗教能为皇家脸上贴金?第四,哪一个宗教有利于扩大版图?第五,哪一个宗教有利于长生不老?第六,如果是一个女皇,他说的是武则天,那么,哪一个宗教能抬高妇女的地位?这恐怕才是佛教在传统中国荣辱兴衰的关键。 但另一方面,禅宗得到精英阶层的认可,"方便法门"也确实是有一定作用,它把自己原来艰深的理论、艰苦的实践、苛刻的纪律都简化了,原本庄严的变得亲切,原本很难的变得容易,原本需要漫长过程的现在一转身就是。但更重要的是,中晚唐五代以后,好多有文化的士大夫进入禅宗,他们把禅宗变得很高雅很有文化,也让禅宗形成玄妙高雅的那一部分内容,你看那些公案机锋,简直就像诗歌和谜语,几乎成了智力较量,这才使得精英阶层有兴趣加入其中。我在《中国禅思想史》的最后,就特别讲这一点,那时候,精英阶层中的人,"在参禅访师的时候,与禅师进行智力和语言的较量,与禅师斗机锋参公案,把话说得富于机巧和幽默,人们的精力集中在语言的暗示性、丰富性和包容性上。他们充分地运用汉语的特征,在生活中讲述一些意味深长的话语,或写出一些含蓄幽默的诗句,这越来越成为上层文化人的业余爱好。在这种时候,它的宗教性就在这些信仰者心中,越来越淡化,倒是它的语言艺术和生活趣味,倒是日益成为信仰者关注的中心。于是,那些精彩绝伦的对话和富于哲理的机锋,也渐渐失去了它对常识和理性的超越性和批判性,成为文人表现生活情趣和文学智慧的语言技巧"。你看,宋代以后喜欢禅宗的杨亿、苏轼、黄庭坚这些人,其实,对禅宗既有人生观的亲近,也有文学上的偏爱。 不过,南宗禅最后成为主流,导致士大夫的禅宗兴趣也南宗化了,这个趋向其实也在瓦解佛教禅宗的宗教性质。过去,历史叙述不是有点儿进化论,就是有点"成王败寇",好像北宗打不过南宗,北宗的文化就不咋地,水平就低一等,所以,我在《中国禅思想史》里为什么特别要特别强调,倒是北宗禅"守住了宗教最后防线",就是因为它还坐禅,还思考,还要经历漫长的修行实践。可是,南宗禅讲"顿悟"、讲"随意",把宗教必须有的信仰、实践和纪律都扔了,当然士大夫们喜欢它,可以让生活很艺术化,有情趣,可是,它就不是宗教了。要知道,一个宗教,在社会中要维持自身的存在,而且要维持人们对它有坚定信仰,你必须要有用,要能指导信众从此岸到彼岸,从沉沦到解脱,不仅要有修行指引的能力,而且还得有一点儿组织纪律。一旦你把原来艰苦的宗教实践变成方便的人生乐趣,把过去深刻的义理学习变成优雅的文学游戏,把严格的宗教纪律变成随意的生活态度,这就很麻烦了。尽管它推动了唐宋以后,士大夫艺术化的人生追求,但是,它也把原来严格的、有纪律的、实践很艰难的宗教信仰全瓦解了。你从此岸到彼岸,总还要跋涉吧,如果此岸就是彼岸,那还要宗教干什么?后来一部分禅宗风格变得含糊甚至狂放,甚至最后没有人对它有敬畏和尊重,恐怕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当然,如果要说为什么在社会普通民众那里,禅宗还有净土,最终会在中国成为佛教最大、最有影响的宗派,在某种意义上说,可能确实和信仰的方便简易有关,坐坐禅,念念佛,就可以和佛陀交易未来,跳脱六道轮回,当然信仰者就比较多,特别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信众就多。只是需要说明,这种方便简易,也会瓦解自身。假如一个宗教,总是门票那么便宜,门槛那么低,恐怕也庄严不起来,它的神圣感也不强烈。也许,在传统中国,佛教不能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强大、独立和有凝聚力、号召力,除了皇权高于一切这个大背景之外,和佛教这种逐渐"去宗教化的宗教"趋向,也有一定关系?这个就是一个需要再探讨的大问题了。

相关阅读扫码查看
<燕京书评>原创稿件,欢迎转发分享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