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中,原訟庭 3 名法官裁斷「五大訴求」不可能達成,政府拒絕回應將成被告無差別否決預算案的「藉口」(見另稿)。而以無差別否決逼使特首對「五大訴求」讓步,雖然不涉武力、本身不構成犯罪,法官仍裁定屬於顛覆罪條文中的「非法手段」。
裁決理據引用人大的「說明」與「決定」,指出《國安法》立法目的是針對「任何」危害國安活動、須健全國安法制,並引「針對禍害原則」詮釋,指「非法手段」的定義既不限於與使用武力相關,亦不限於構成刑事罪行的行為。
官並引本案起訴後生效的《釋義條例》條文,裁定無差別否決足以構成濫用權力,違反《基本法》規定,故屬非法手段,辯方的法律爭議全部被駁回。官亦進一步裁定,控方毋須證明被告知悉行為屬於「非法手段」,指「否則被告即可基於自己對法律無知,提出辯解理由」。
判詞分析1|初選被指違法的核心 原訟庭3法官:五大訴求不可能達成
47人案追蹤專頁

判詞:《國安法》目的針對「任何」行為
本案罪名是《國安法》第 22 條顛覆國家政權罪,法庭需詮釋由人大常委會制訂的條文。控方原本指被告「以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嚴重干擾政府履職,但開案前刪去「威脅使用武力」,僅餘「其他非法手段」。
據指定法官陳慶偉、李運騰及陳仲衡撰寫的裁決理據,他們引用 2020 年 5 月 22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說明」,以及全國人大同月 28 日通過制定《國安法》的「決定」,指均提及立法目的是針對「任何」危害國安的活動。
辯方曾爭議,應採用普通法「同類原則」詮釋,即顛覆罪的「其他非法手段」應承接前段脈絡,定義是限於與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相關。
法官反駁指,若如辯方狹獈地詮釋,將會有違《國安法》立法目的,又指不難預見可透過不涉武力的方式癱瘓立法機關,例如攻擊資訊系統、立會人員亦會受生化或放射性物質攻擊影響。
對於辯方指,上述例子的行為受《國安法》其他罪行,例如恐怖活動罪規管,法官再反駁指該罪與顛覆罪目的截然不同,前者是針對脅逼政府,後者是保護根本制度、政權機關。官最後引「針對禍害的原則」(mischief rule),指「非法行為」不限於與使用武力相關,否則「是不合情理、不合邏輯且有違《國安法》目的」。
判詞引《國安法》第一條 須健全國安法制
法官接着處理「非法」的定義,引《國安法》第一、三及六條,指須健全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香港特區負有維護國安責任,以及香港居民不得從事危害國安的行為和活動,故所有旨在顛覆的行為,「不論其形式及方法,均不可能視為可接受或可容忍的。」
對於辯方爭議「非法手段」必然指可構成刑事罪行的行為,否則會造成顛覆罪過於廣泛和有欠肯定,例如民事過失都會被涵蓋,法官反駁指人大在條文沒使用「犯罪手段」(criminal means)字眼,而選擇「非法手段」,用意明顯與辯方的說法相反。至於民事過失是否足以構成「非法手段」,法官認為毋須在本案表達肯定意見。
法官亦分析《國安法》第三章,指「非法」一詞在不同罪行的條文總共出現 5 次,綜合理解可包括違憲、違法,或不符正當程序的行為,構成一般意義的「非法」(unlawful in a general sense)。
官續指,「正確地詮釋」第三章的條文後,結論是顛覆罪的「其他非法手段」,不限於刑事行為,目的是要建立健全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以及防範顛覆罪。
在審訊中,控方提出「非法手段」有兩個層面,其一是「公職行為失當」罪。辯方反對,並指該罪與顛覆罪完全不同,而控方中途提出做法極其不公。法官在裁決理據未有提及控方主張「公職行為失當」罪一事,亦未有作裁斷。
判詞:無差別否決足以構成濫權
在裁定「非法手段」不限於為刑事行為,並可包括違憲後,法官進一步裁斷,案中以無差別否決預算案逼使特首對「五大訴求」讓步,足以構成濫權,違反《基本法》規定。
判詞指在《基本法》下,立法會議員「顯然集體肩負憲制責任,在需要時依據財政預算案的利弊,對之審核和通過」,又指《基本法》亦要求立會議員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
法官接續指,因此「不予區別地否決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公共開支,以迫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向來都違反《基本法》第 73 和 104 條內擁護《基本法》的規定」。
審訊時,控方提出「非法手段」的第二個層面是濫用職權。辯方多人爭議,例如陳志全代表大狀馬維騉稱議員沒被禁止否決任何議案,包括不顧優劣地否決預算案;何桂藍代表大狀 Trevor Beel 稱,《基本法》沒限制立法會如何運用審核預算權力。李予信的代表大狀關文渭則稱,若被告因預算案內容沒回應「五大訴求」而否決,就不能指控他們沒有審核內容。
法官在判詞中未有逐一反駁,指立法會雖然不應「自動、機械式地」通過政府的預算案,但認為大多數議員不論內容優劣地蓄意否決,是「明顯違反《基本法》第 73 條及《國安法》第三條」,足以構成(would amount to)濫權。官另反駁辯方,指被告是在當選前達成協議等,故議會特權不適用。

官引起訴後生效《釋例》 指支持濫權闡釋
法官另引用《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3AA 條,指訂明「無差別地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議案」,意圖以此逼使特首下台及推翻政府等行為,不屬擁護《基本法》。官指,該部分支持他們對被告行為可構成濫權,從而屬「非法運用立法會權力」(unlawful use of the power of the Legco)的闡釋。
不過辯方在審訊時爭議,該條文是在 2021 年 5 月,即被告在本案被起訴後才生效,對本案沒追溯力。控方當時指,該條文是將既有的定義訂為法例,又指被告的行為從常識而言不會是合法。
法官在判詞接納控方的說法,指該條文雖沒追溯力,但只是清晰解釋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律要求,鞏固過去的原則,「沒有添加新事項或概念」。
官續說出結論,重申無差別否決預算案或公共開支,以逼使政府回應「五大訴求」,「向來都違反」《基本法》的規定,又指「若此等行為具有嚴重破壞政府或行政長官權力和權威的意圖,更不在話下」。

官裁定毋須證被告知手段是非法
辯方亦爭議,控方必須證明被告在案發時,知道涉案行為屬「非法手段」,才能達致定罪。而多名被告都供稱,相信戴耀廷稱否決預算案屬《基本法》賦予的權力;亦有被告引述行會成員葉劉淑儀、資深大狀湯家驊等曾稱初選不違法。
法官在判詞駁回辯方,指「非法」一詞,「明顯是形容罪行中的犯罪行為」,而非犯罪意圖,「否則,被告即可基於自己對法律無知,提出辯解理由」。官最後裁定,控方只須證明被告知悉涉案行為會造成嚴重干擾政府履職,而毋須證明被告知悉涉案的手段是非法。
官又指,顛覆罪不是「絕對法律責任」罪行(即毋須證明犯罪意圖,法律 101 文章),而是「帶有特定意圖的罪行」(an offence of specific intent),故此,控方除了須證明被告有意圖落實涉案手段外,亦須證明被告作出涉案行為時,旨在顛覆國家政權,否則不能定罪。
HCCC69/2022
文章来源:法庭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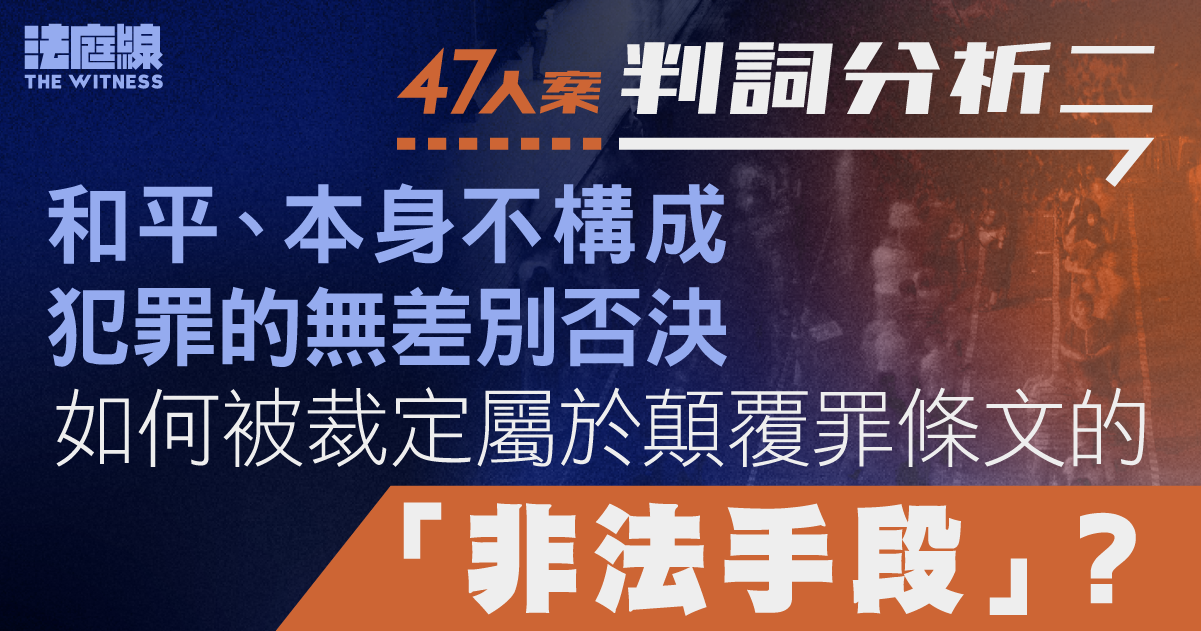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