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启蒙运动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努力,然而,现实的不平等却愈演愈烈……为什么我们越是奉行平等理念,现实中平等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平等”无疑是奠基现代社会的重要原则之一,而且深刻地体现在我们社会生活中以及制度之中。作为一种现代的意识形态,“平等”天然地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因而近代历史上的那些激进的政治实践,也大多挪用乃至曲解了平等的含义。
然而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平等远远不止于一种统摄着意识形态的观念,平权运动和性别平等,我们发现对“不平等”的存在越来越敏感,而且越来越多难以察觉的不平等则层出不穷。“结构性不平等”这样的词汇,越来越多地被使用描述今天的世界。但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平等”这一个贯穿人类历史,具有无穷的道德感召力的感念?而我们时代的“平等”又与不同时代思想家所处理的思想概念有着怎样的内在连贯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EHESS)哲学与社会科学博士新书《平等悖论》,带领我们回到理论源头与思想史现场,从“自然-本性”“财产”“进步”“契约”四个方面,逐步拆穿那些看似理所应当的观念背后的矛盾与陷阱,寻找当今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症结所在。本文为谢晶《平等悖论》一书《走出为平等而平等的怪圈》,标题为编者所改,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 谢晶
出版社: 光启书局
出版年: 2026-1
页数: 364
定价: 78
装帧: 精装
丛书: 差异与共生
ISBN: 9787545220551
试图用统治的逻辑去实现平等,是出现“平等悖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4年,黑人女性主义作家奥黛丽·洛德( Audre Lorde)应邀在一个女性主义研讨会上发言。面对黑人女性、第三世界女性和同性恋女性的缺席,她愤怒地说:“主人的工具永远不可能拆掉主人的房子(The master’s tools will never dismantle the master’s house)!”
洛德愤怒于学院女性主义者忽视非白人和非异性恋女性的经验和思考,不关心这些女性写了什么,也不反思当她们自己参加女性主义会议时,在她们家中从事家务并照料孩子的大多是有色人种女性。洛德称,学院女性主义批判男性统治,但她们对其他女性经验和思想的无视,乃至对她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是在复制男性统治的逻辑。
如果女性主义一方面批判男性统治的社会将男性经验等同于 “人”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忽略女性内部的经验差异,将一类女性的经验等同于唯一值得被命名和探讨的女性经验,如果女性主义一方面指责男性出于统治者特有的无知而对女性的思想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又不关心非学院/非精英女性的言论和创作,如果女性主义一方面指责男性对于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剥削,另一方面又将这些劳动“外包”给其他群体,那么这就是在想要“拆掉主人的房子”的同时,仍然持有与主人一样的工具。
“主人的工具”是那些用来为统治关系建立正当性的观念和逻辑,它们让一部分人的经验变得无足轻重、不可言说,迫使其服从、被剥削—这就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实质。如果女性主义以此为逻辑而企图实现平等,等于是在用主人的工具企图拆掉主人的房子。然而,主人的工具是用来造主人的房子的,它们只会令主人的房子更牢固,只会令统治和压迫、歧视和管控更有效。
不仅在女性主义思想史上,而且在更广义的平权史上,“主人的工具永远不可能拆掉主人的房子”都已成为振聋发聩的口号。 它还从口号变成一个极为珍贵的方法:任何以平等为理念的人都 应该不断审视自己是否不自觉地拿着巩固阶序和特权的工具妄图 推进平等。
在这本书中我想要呈现的,也可以说是一番寻找“主人的工具”的历程。我试图证明,支撑起现代平权理念的那些主要观念,都无不落入“用主人的工具拆掉主人的房子”的悖论。自然与文化、感性与理性的二分与排序,世界的机械化,具有排他性的财富积累,社会关系的泛契约化,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内的所有关系的量化和可操控化,所有这些启蒙思想用来证明人的尊严与自然权利,并证明平等的正当性与可行性的观念,都更适用于建立阶序,而不是平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现代化的进程恰恰就是这些观念深入我们的惯习,建构 我们的认知并主导我们行动的过程。这是造成我在“序幕”中提出的“平等悖论”(我们奉行平等,平等却变成海市蜃楼)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本书的第一重结论。
从“平等悖论”到“做人悖论”:现代性是一个大写的悖论
就在本书写成之际,“做个人吧”和“把人当人吧”正在我 们的舆论中成为越来越高的呼声。就像不平等在当今社会愈演愈烈一样,这些呼声本应令我们感到匪夷所思。“人本主义”难道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面最重要的旗帜吗?文明和进步的最终目标,难道不是人的彻底解放,人性的彻底实现吗?那么,为什么在现代化如火如荼地进行了这么多年后,我们却如此强烈并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不是在做人,也没有被当成人来对待?这构成了一个与平等悖论高度类似的悖论:为什么我们越是高举人本主义的大旗,社会就越是缺少“人味”(让我们称此为“做人悖论”)?
我们为“平等悖论”找到的观念上的原因同样也适用于“做人悖论”。启蒙思想要证明人类具有共同本质,却将这个本质从人类明明所是和所处的自然中孤立出来,令理性和算法与生命分道扬镳;它强调凡是人都有的能力和应有的权利,却把这些能力和权利树立为征服和占有、利用和控制,我们被定义为用算法实 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就好像再没有其他事情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并被我们视作有意义,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渐渐呈现 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让竞争和占有变得更公正和有序渐渐成 为建立社会关系的唯一目的,契约和法制于是成为建立社会关系的唯一模式。而在由合法暴力保障的、越来越烦琐的法律和制度中,每个人所能采取的最合理的行动,似乎也就唯有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做征服者和享乐者,去生产和消费。与此同时,每个人也在他人试图达到这些目的过程中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和资源。无论是用算法去征服和榨取的“经济人”还是被算法征服和榨取的“人力资源”,都离我们真正所是的那个人越来越远。“做个人吧”和“把人当人吧”所表达的,正是当代人对于自身“非人”处境的体察。
对于平等悖论的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适用于做人悖论,是因为启蒙精神递到我们手中的,是同一套工具。同一套工具令人试图实现一种“非人”的“本性”,又令这个实现本性、争取权利和建立关系的过程,总是关乎阶序,而不是平等。算法加上竞争的结果,是不等号而不是等号。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主人和征服者——只有在主奴关系中才可能存在主人。
如果同一套工具造就了上述两个悖论,那么它们毋宁说是同一个悖论的两面。归根结底,现代性可能就是一个大写的悖论。它可以表述为“平等悖论”——为什么我们追求平等,不平等却愈演愈烈;也可以表述为“做人悖论”——为什么我们在高举人本主义的同时,却不再“做人”,也不再“被当作人”;还可以表述为“自由悖论”——为什么“自由”成为一种主义,我们却困在系统中;“技术悖论”——为什么我们发明技术来解放人,但是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被技术塑形;“富裕悖论”——为什么财富 总量越来越多的我们,却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越来越匮乏,比如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和无污染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关爱, 甚至还有对周遭世界的感知方式,对共同生活的想象力……所有这些,是否都是同一个悖论的不同面向?是不是同一个主人的工具箱在不同的场域中被“批量生产”?是不是同一套“矩阵”,也 即同一套深层的逻辑——对立和排序,机械化和算法化——在不同的现实层面和不同类型的关系中,幻化为一整套意识形态和一整套惯习?
我们陷入了为平等而平等的怪圈
“做人悖论”不仅提示我们“平等悖论”可能只是一个更大悖论的诸多维度之一,是现代性困境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它提 醒我们平等理念正在走入何种误区。关于平等,我们几乎只问可能性的问题:平等究竟有没有可能被实现,又如何可以被实现?我们几乎已不再问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要实现平等?不再被追问为什么,这是所有政治正确的理念的宿命。但如果说“做个人吧”和“把人当人吧”是当代人对于一种普遍不幸的表述,那么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就算平等是可实现的,就算我们搞清楚了实现它的方式,如果其结果是人的“非人化”,是我们获得尊重和关爱的根本需要普遍地得不到满足,是 我们最根本的脆弱性被彻底无视,那么这样的平等还是值得追求的吗?
“做人悖论”提醒我们,在海市蜃楼的“平等悖论”背后,还 存在着一个平等盲点:我们把平等变成了一个绝对的好东西,一个终极的目的。可是平等本身难道不是一种手段?它是人与人建立关系的一种模式,但它并不告诉我们,当这样的关系建立起来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群体生活,人们可以一起从事些什么。
换一种说法, 我们在平等的问题上犯了一个语言错误,“equality”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它并不对应任何的东西,而是从形容词“equal”和副词“equally”延伸出来的,我们在语法上需要出现名词而不是形容词时使用它。而形容词和副词“平等的/地”是需要被补足的:平等的什么?平等地做什么?将平等用作抽象名词的政治话语渐渐地将平等从手段变成了目标。在中文中现在也有一模一样的误导。
在我们的平等理念下,如何补足作为形容词和副词的“平等”?如果平等意味着平等地运用理性和算法,平等地遵循规则,平等地竞争和占有,那么我们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所首先实现的,就是今天我们在经历的平等地不做人,平等地变成机器、变成孤岛,平等地不相爱,平等地倦怠、无聊、不幸……这样的平等,是值得追求的吗?
不再追问平等是为了什么,这令我们陷入为平等而平等的怪圈,然而当我们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而得以补足“平等的……”和 “平等地……”,我们发现,我们的平等理念会引发严重的观念失效,它即使是可实现的,也不见得值得追求—这是本书的第二重结论。
我们的平等观颇为特殊
以上两重结论都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放弃对平等 的追求呢?
在“序幕”中,我曾援引《人类新史》对现代平等观之缘起 所做的大胆假设(让我们简称为“《新史》假设”):美洲原住民对欧洲社会的批判是启蒙时期平等观的重要来源。确切而言,这只是《新史》假设的一半,它的另一半是:启蒙思想家并非照搬 了这些原住民批判,而是通过塑造自己的平等观念去回应和反驳它们。
完整的假设因而是这样的:原住民批判所针对的不仅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极端不平等,不平等甚至都不是最首要的议题,尤其被美洲原住民视作荒谬和罪恶的,是私有制、法律、和奴役。我们还记得,这些恰恰是卢梭为人类的堕落和不幸所找到的主要原因:堕落和不幸始于财产的划分,经由法律和政府的建立,最终变成所有人都失去自由而必须服从“利维坦”的状态。换言之,对于原住民和深刻认同了原住民批判的卢梭而言,不平等就自身而言并不是绝对的恶,其结果才是,这些结果中尤其包括奴役、不幸和道德上的堕落。
然而,其他的启蒙思想家并没有卢梭那么激进,他们并不想全盘推翻正在兴起的、建立在私有制和法律之上的“文明”,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用原住民价值观来证成自身文明的策略。平等这一原住民所信奉的价值现在成为启蒙的最高价值,但与此同时,受到原住民批判的财产和法律现在被证明是实现平等的途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于是就产生了今天被信奉的财产主义和契约——法律主义平等观。通过将原住民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原则(平等)放到首位,取消其他原则(例如共同主义的原则和拒绝极权的原则),欧洲文明得以证明自己手中才掌握着实现理想社会的奥秘(而原住民反而变成了无法实现此理想的野蛮人)。这就是《人类新史》对于启蒙精神的颠覆性解读:它是一种应激反应,一种抵制其他社会模式的策略。
《新史》假设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平等观会有“用主人的工具拆主人的房子”的矛盾:它原本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自己所披上的平等主义外衣。由此,《新史》假设也提示我们,我们今天所持有的平等观是一种颇为特殊和狭隘的平等观。这意味着其他 平等观是可能的,这意味着对它展开改良的工作(参见第一章第1节)是可能的。我们可以以其他的方式构想平等,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平等是值得追求的?除了平等地竞争、占有、计算、立法和守法,我们还能平等地做什么?
改变观念有很多方式
如何改变观念?这是一个令从事意识形态批判的人望而生畏 的问题。因为就像制度一样,观念不会无中生有。作为处于特定 社会史并具有特定惯习的人,我们能用来构想新观念的似乎只有现有的观念。但是这样的话,想要拆掉主人的房子不就彻底不可能了吗?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妄想无中生有地创造观念,那么只可能像自以为跳出了如来佛手掌其实只是在佛祖手中撒了尿的孙悟空,自以为创造了新的想法,其实只是换一种方法耍弄主人的 工具而不自知。
想要跳出的前提,是看到佛手的边界。因此,意识形态批判 在看到观念很难发生变化的同时,也走出了改变观念的第一步。看到主人的工具,其特定的逻辑、其特殊的起源、其效力所及之 处,也就是看到“反工具”的可能。当卢梭针对理性主义将怜悯 心奉为道德的来源,当他针对进步史观写下堕落史,他正是在践行这种在水平方向上更新观念的方式——尽管将理性对立于怜悯难免陷入二元论的矩阵,堕落史仍然落入线性史的窠臼,但这仅仅表明,观念的更新既然不能无中生有,也就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只可能是一个缓慢离心的过程。
正是这种到边缘探索新观念的方式令当代的平等主义充满生机。看到在主人的逻辑中,理性是至上的,它凭一己之力令人获得真知和德性,那么我们可以去关注感性在认识和德性中发挥的作用,关注感性与理性如何共同作用于我们的判断和行动。看到主人的逻辑通过对理性与感性、文化与自然的排序令再生产者处于弱势,我们可以试图取消或颠倒排序,去强调关怀(care)对 于作为生命体的人来说比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具有更高的价值。看到主人的逻辑对于契约和法律的强调,我们可以去发掘其他类型 的社会关系——那些被忽视和遗忘的、建立在共情和互助之上、没有评估和算法、随时可以协商和调整的关系。当我们发现主人的逻辑是竞争,我们可以强调共生……
这种培植新观念的尝试甚至不一定要在当下人类的政治领域展开,不一定要以我们当下的关系与行动为对象。如果说是同一个“矩阵”在不同的现实层面与关系类型中幻化为一整套对于世界的认识和一整套惯习,那么,对于任何常识的挑战都可以是对于深层“矩阵”的撬动,都可以令我们意识到社会关系可以以 其他方式展开。关于过去,我们现在知道要到线性史(History)的单行道之外去关注那些被压抑的故事,去关注女性的“她史” (herstories)和非精英—统治阶层无文字记载的口述史,试图令 所有的经验都获得被讲述的机会。看到主人想要将一切都塞入因果关系和一成不变的规律中,将一切都变成世界这个大机器中的 一个齿轮,我们可以去关注那些塞不进因果关系中的“怪象”,看到无处不在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
当代动物行为学是通过撬动认知而撬动观念的典范——因为我们曾经在动物身上投射了我们对于自然的所有偏见和对于人类 社会的所有构想,我们曾经把这些构想直接变成自然界的事实。 曾经,动物行为学家“证明”动物(只)有模仿能力是因为人类 被视作唯一有创造力的物种;“阿尔法雄性”的提出是研究者将 男性主导的社会模式投射到灵长类群体,并且是为了证明社会阶 序就像自然法则一样属于不变的定律;而动物行为实验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动物的机械本能,只是因为在实验室的刻板 环境中,刻板行为必然如期而至……当对于主人的工具产生怀疑 的动物行为学家渐渐意识到这一切,他们开始像人类学家一样, 到自然环境中观察动物,将每个动物视作不可复制的个体,而不 是一个物种的千篇一律的样本,甚至于开始彻底地改变动物行为 学的提问方式,将“动物有没有这样或那样的本性/能力?”替换为“对于它们而言什么是‘有意思的’、‘重要的’、值得‘回 应(response)’的?”(参见第二章第2节)当动物由此从刻板 的机器重新变成有回应周遭世界能力的生命,当科学方法从控制变量的实验变成了相互了解和回应,当根深蒂固的认知这样被颠 覆,我们原本与世界和与他人相处的刻板方式也会开始瓦解。重 新将动物当作动物(而不是有着固定属性的东西),这也会反过来让我们重新看到,将人对待为人(而不是有着可量化价值和能力的东西)意味着什么。
所有这些水平拓展边界的尝试都常常让人发现,“反工具”已 经在那里了。找到新观念的过程其实常常是重新发现被遗忘的观念的过程,因为在同一个观念的生态中,占主导的意识形态之外并非真空。无法被纳入同一个矩阵的那些“叛逆”的观念并非尚不存在或不再存在,它们就像一些稀有的物种,或尚未开花结果的种子。它们可能就在各种“ta 史”和各种被视作不“科学”的认识方式中,各种被视作不“体面”和无意义的关系中。让观念发生变化,并不需要无中生有,而可以是打破占主导的知识和惯习的特权,令观念的生态发生变化,为那些边缘的、没什么人采纳的、被认为不值得注意和不配生长的观念,重新找到土壤,用 我们自己的思考为它们提供养分。
即使当观念的生态在越来越单一的社会模式之下,就如单一作物下的生态环境一样,渐渐变得贫乏(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无可否认的后果),有一种水平拓展的工作令观念更新始终可能,它是人类学家的工作。当人类学摘掉“愚蠢而悲惨的野蛮人”的有色眼镜,看到生产方式乃至于作物类型都不仅仅取决于 客观条件,而可以是一个群体的选择,看到在有的群体中,人们的全部努力并非为了建立规则并让所有的人执行,而恰恰相反,是为了防止制度和权力被稳定下来,看到努力满足每个成员需求 的社会既不必须建立法律也不必须建立财产,他们通过了解其他的观念生态,来告诉现代人,其他的社会理念是可能的。
这些其他生态恰恰凸显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平等观:它并不建立在对于东西的排他拥有和对于法律的制定和遵守之上,而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服从或不服从,意味着每个人在集体决策中都能有所表达并被听到,意味着每个人的需要都被看到。当财产——法律主义的平等观令自由与平等形成矛盾并令人愿意为了后者牺牲前者(因为财产权的建立需要法律和合法暴力的强制保障),这种存在于现代社会之外的平等观不仅不与自由构成潜在的冲突,而且自由就是平等的最终目的。这正是卢梭为我们提供的最终解药:平等需要被补充为平等地自由,也即没有人需要臣 服于其他人的状态。
“当平等地不做人”成为我们平等观的症结,所有这些观念更新的尝试恰恰令我们看到“平等地做人”的可能,看到一种不建 立在数学等式之上,却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人,将每个人当作人来对待的平等观:将每个人对待为有不同需求和意愿,有生命力和行动力,但同时也有着脆弱性的人,并将“令彼此成为完 整的人”视为人们联结为社会的意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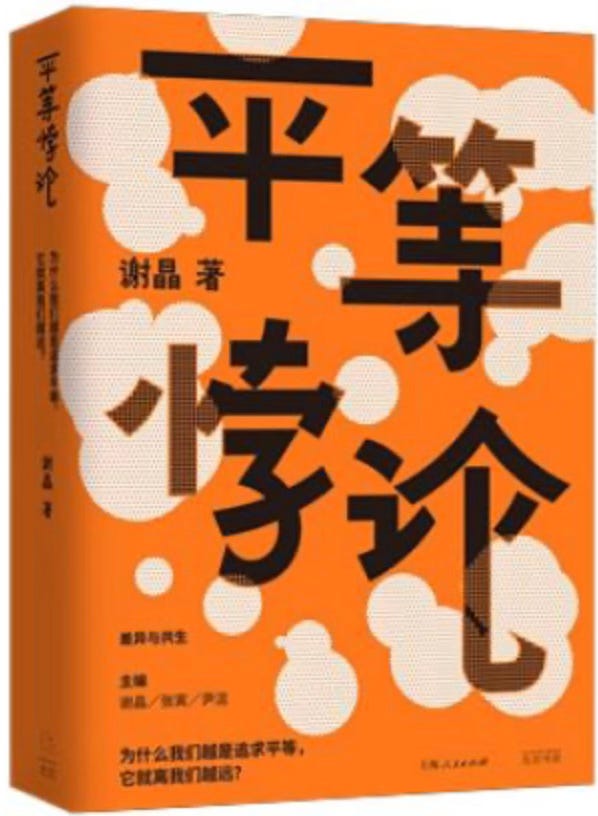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