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著名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8月1日晚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
余英时先生1930年出生于天津,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香港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学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各地任教,晚年寓居在普林斯顿。
在学术上,余英时专治思想史,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通古知今,成为21世纪罕见的史学泰斗。2006年,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又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同时,余英时先生持续关注现实、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他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学者的深邃眼光,使其成为当下华语知识分子的典范。
2018年,记者曾两次到余英时家中对他进行采访。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2018年4月,记者首次前往余英时寓所采访近三个小时,当时,余先生正在写他的回忆录。余先生也给记者回忆了当时他离开中国的情景。他说,本来他在燕京大学读书,寒假的时候去看香港探望父亲,休假结束后就做火车回北京,火车还在广东的时候,他突然想到父亲年龄大了,又跳下火车,买了黄牛票,从罗浮桥又回到香港,那一年是1950年。
余英时这一走就是29年,直到1978年10月,余英时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真正体味到城郭如故人民非,虽然也激起过他的中国情怀,但是亲朋好友的故事让他越发有一种化鹤归来的感觉。1989年后,余先生立誓不回大陆,并说:“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对此,青年学者羽戈说,这句话仿自德国作家托马斯·曼。1938年初,曼流亡美国,对记者说:“这(流亡)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说到文化,余先生还有一句名言:“哪里有自由文化,哪里就是我的故乡。”这则可呼应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虽然,余英时先生曾表示,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是,他非常看重自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历史与思想》自序中,他曾援引美国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的话说,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信持之下,余英时先生成为当代华人世界中持续关注现实、坚持在公共领域发声的知识分子。
关心中国时政 不做不问世事书斋人
在访谈中,余英时对当下中国时政非常了解,甚至包括当下被严密镇压和审查的群体性事件。他说,几年前,大陆媒体比较自由时,经常报导每年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有时竟至十几万次。近几年来,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厉,我们已读不到这类统计数字。但相关信息仍然不绝于耳,例如最近卡车司机联合大罢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号,上海、山东、重庆、广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机都起而响应,显示出危机蔓延之广。以中共的专政力量,它也许能把这些个别的抗议和危机一一压制下去,但这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压制可以永远成功。专政一天比一天加紧,正是它“害怕”的反应,所谓“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掩饰“害怕”。
因此,余英时说,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他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创办人、前总编辑程益中说,余英时先生对我最大的激励便是他对时政的关心,他不是那种不问世事书斋中人,对当下中国、对中共政权的过去现状和未来都有着深切的关怀,这对于读书人来说是莫大的鼓励。2018年12月,程益中曾去拜访余英时先生,程益中记得,余英时先生对他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新闻,新闻就是现在的历史,历史和新闻两门学科之间是相通的。这让程益中受到莫大鼓励。
在得知余英时先生去世消息后,因六四流亡海外的作家苏晓康在fcebook上回忆了余英时陈淑平伉俪多年来对他的帮助,他写到:“掐指已三十年,只觉得沐浴余先生之春风,享受的丰厚教益是一生都用不尽的;尤其我和傅莉,在劫难中得到余英时陈淑平伉俪的坚实慷慨的扶助,恩德重于山。这一番普林斯顿的际遇,一位大师级学人赐予我们的,不止精湛的知识,还有更伟大的人格力量,我的「六四流亡」因此而成莫大幸运。”
王丹回忆说,1989年六四之后,大批知识分子逃亡海外,余先生出面争取到大笔捐款,成立了“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收留和保护了很多流亡的异议人士,这一点广为外界所知,不需我多言,但必须一再提起,而且最令我动容的是,当时美国在首都华盛顿成立了自由亚洲电台,这是中国流亡异议人士聚集发声的平台,政治色彩鲜明强烈,而余先生完全没有因为这点而有所顾忌,长期以来,一直是自由亚洲电台的特约评论员之一,而且就跟他做学问一样,一丝不苟,兢兢业业,持之以恒。
“中国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史学危机”
作为历史学家,余英时非常关注当下中国的历史研究状况,他告诉记者,国内重要的历史刊物,每一期他都会看,国内稍微好一些在历史研究著作也会看。在访谈中,他拿起看了一大半的齐小林博士的新作《当兵:华北根据地农民如何走向战场》说,这本书不错,是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看的,我看了确实是不错。
不过,余英时认为,中国当下虽然有零散好的历史研究著作,但整体来说,面临一个很严重的史学危机。
他说:“这必须从中国现代史学的萌芽说起。从清末民初,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倡新史学以取代以前的王朝史,中国史学已踏上了现代化的台阶。再经过“五四”新思潮激荡,特别是其中“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长期进展,中国史学面貌为之一新。钱穆先生回忆他在三十年代北平和当时学人如陈垣、秦公权、杨树达、向达、贺昌群、张荫麟等交往的情形说:’要之,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这一段话,字字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态。我现在抄录它,也不胜感慨。而且即在抗战期间,第一流的史学著作仍源源而来,举其最著的例子,便有陈垣有关佛道两家宗教史的研究,陈寅恪对隋唐制度和政治的专论,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董作宾的殷历谱,钱穆和张荫麟的两部史纲等。但自1949年起,中国史学研究遭遇到了空前的厄运。斯大林的’五阶段论’(收在《苏联共产党简明教程》中)成为人人必遵的全科玉律以后,史学研究者已完全失去了构思的自由,任何带有思想性的历史论断都必须以斯大林的教条为依归。所以在整个毛泽东时代(1949-1976),史学家的主要工作只能集中在史料编辑方面;而由于编辑的原则仍出于教条,材料的收集也漏洞百出。我们今天检查一下这三十年间出版的规模加大的史学书刊,便立即会发现,当时史学家所付出巨大劳动力,完全是白费了。苏联崩溃之后,俄国史学家回顾1917年以来的历史书籍,坦承七十多年来的史学真是一片荒芜,没有一部书在今天还有阅读的价值。中共的情形也如此。”
文革结束后,中国政治情况虽然稍微改善,但余英时先生认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危机依然存在。
他说,1980年代以来,教条的拘束力虽然也有所松动,但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依然如故,构思的自由并没有显著的改进。最近由于政权统治的体制发展到了顶峰,意识形态对于史学研究的干预也随之加紧了。有两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所有研究经费都控制在“党”的手上,只有对“党”有力的史学论题才能得到慷慨的支援。至于寻求历史真相但有损“党”的形象的研究计划,则必然落空,而且即使写成了也很难发表。这是我从许多国内大学的史学教授那里获得的讯息。第二,最近《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大学(如清华)更加强了灌输意识形态的努力,而“中国现代史”则是其中五项课程之一。这样一来,中国史学就更遭殃了。我们都知道,中共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一向以宣传“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为主旨。但其中也有阶级性的差异。早年在延安,尚未得政权,范文澜编中国近代史尚不敢过分宣传,因为他出自黄侃门下,受过国学训练,毕竟有所顾忌。1949年以后,历史课本便越来越走向宣传的路。到了1966年所谓“文化大革命”,历史则完全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用谎言来抹杀事实真相已成为常态。今天作为大学中意识形态课程之一的“中国现代史”便是彻头彻尾的伪史。中共已正式宣布对于毛统治下的三十年不许有任何负面的评论,对于毛死后至今的三四十年更不许稍有“妄议”。试想在这样的装填下,今天青年学生所能接触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知识”呢?写史必须用“直笔”,不能隐藏或歪曲事实,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之一,所以,董狐“书法不隐”,孔子特别称赞他是“古之良史”。后世朝廷史观在《起居注》中记载皇帝的言行,无论是善是恶,也都援事直书。唐太宗想看他的《起居注》,便为史官所拒绝。古今对照,不但中国史学危机的深度显露无疑,而且中国极权统治怎样摧毁传统文化也得到了一个具体的说明。
中国现代学术一个“典范”
余先生师从国学大师钱穆,钱穆显示晚年《师友杂忆》一开始有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余先生坦承:“东西文化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我的学术生命。但我比钱先生迟生三十多年,具体关注的问题当然同中有异。”
在余英时先生看来,钱先生着重“东西文化”的“得失”和“优劣”, 而余英时先生关注的是文化异同的问题。在余英时看来,与文化异同密切相关的则是历史变化的问题。“总而言之,二千年不变的历史论断对我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因此寻求这两千年间的历史变动,终于成为我早年治史的重点所在。既然以变动为出发点,在某些问题上,我也不得不上溯至古代或下及于现代,以‘通古今之变’。”这可以说是余先生一生学术脉络所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自1950年代出版著作始,余英时先后著有中英文学术著作数十本,其中,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有:《汉代贸易与扩张》、《方以智晚节考》、《历史与思想》、《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史学与传统》、《陈寅格晚年诗文释证》、《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钱穆与中国文化》、《现代儒学论》、《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等,其学术研究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清代中期,涉及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等,涉猎广泛的研究也不是无的放矢,“我自早年进入史学领域之后,便有一个构想,即在西方(主要是西欧)文化系统对照之下,怎样去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色。”也正是从这个构想出发,余英时先生展开了他一生的历史研究。同时,他出入古今中西的学习经历,也让他得以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学术进行沟通对话,并由此建立起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典范”:既为中国传统现代化开新路,也留下了无数的工作让后人继续:中国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现代儒学的发展等等。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这样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库恩所说的新‘典范’。而且这个‘典范’约略具有库恩所说的广狭两义:广义地说,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方面,他的具体研究成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起了‘示范’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
这段话用来评价余英时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是非常准确的: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了一个“典范”。
台湾中央研究院在余英时去世通告中评价余英时是“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罕见。”大陆青年学者羽戈有一句著名的话:“老辈看余英时,中生代看秦晖。”在他看来,“这两位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
澳门大学历史学教授杨斌说:“余英时的学术研究,既受到钱穆当年深厚的国学训练,又受到杨联陞新史学的培养,可谓得到新文化语动新旧两派的嫡传。这对他以后能以同情之心来理解陈寅恪、方以智以及朱熹大有裨益。我最初接触到余先生的著作是他博士论文汉代的贸易与边疆扩张。这是研究一本汉代经济贸易史和边疆史的著作,所以我本人研究西南边疆颇有启发。尤其值得注意但被学界忽视的是,余英时在这部1967年出版的 著作中提出了在边疆地区存在的Sinicization 华化和Barbarization 胡化的两种现象。几十年后的关于所谓‘新清史’的讨论中,几乎无人提到余先生多年前的贡献。以后余先生的主要经历在于思想史和文化史,这是一个通古知今的大家才可以专注的领域。”
在杨教授看来,无论从自我的精神世界,或者外在的期许仰慕,余先生已然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他的逝去,令人不由得再次忧虑中华文脉的断裂和延续。
文章来源:VO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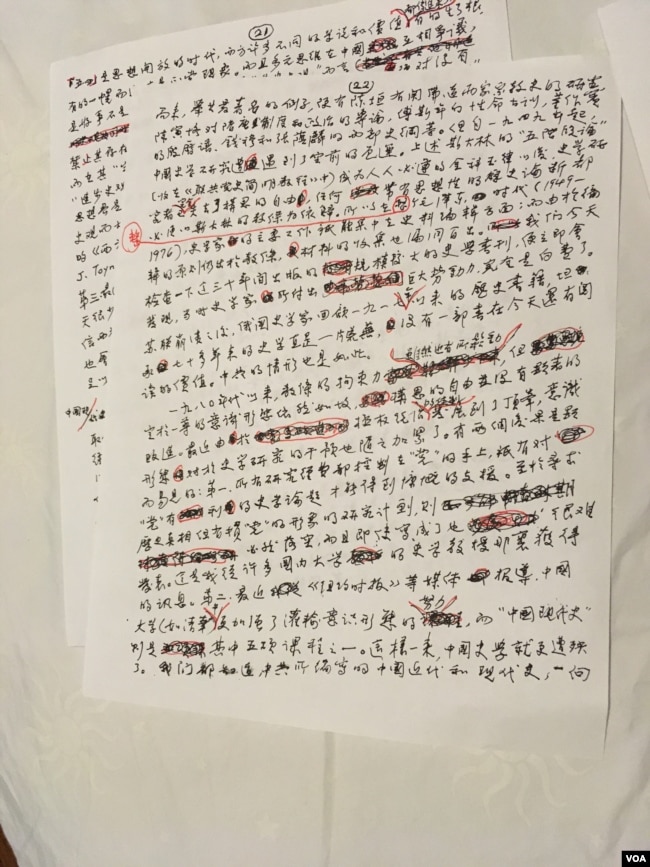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